周拥军:对联的精气神
“精气神”是文学艺术力和生命力的重要体现。如果将“精气神”分而论之,“精”就是精华、精炼等。《说文》云:“精,择也。”换句话说,“精”是对思想深度的锤炼,是一种语言艺术手法。“气”就是气贯、气象等,是可以为人外在感知,内在体悟的一种状态;“神”就是神采、神韵等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中说:“得神者昌,失神者亡。”对于对联创作而言,也是如此。
一、精
吴恭亨《对联话》中说:“左文襄题祠庙各联,精神团结,一字不懈,亦一字不苟。”《词洁辑评》云:“句意警拔,多由于拗峭,然须炼之精纯,始不失于生硬。”在对联创作中,我认为的“精”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:一是精炼;二是精当;三是精深。下面我们便分别展开来详细阐述。
先谈“精炼”。精炼一般是指语言精练,主要体现在炼字上。唐代诗人贾岛《题李凝幽居》诗:“鸟宿池边树,僧敲月下门。”大家都知道“推敲”的典故,一个“敲”字,铿锵有声,使意境陡升。其实,“鸟宿池边树”一句也有商榷之处,此句是古时编者所改的,原诗为“鸟宿池中树”。我认为“中”字比“边”好,“池中树”乃树影在池中,鸟宿池中之树影,意更曲折,亦有余味。况且对联字数本身较少,作联更要炼字,每一个字都要“以一当十”“一字千钧”。下面就以拙作《题寒山寺》为例说明:
钟声敲落三更月;
霜色铺平万里秋。
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曾说,“以最小的面积,表达最大的思想。”此联中“敲”“铺”二字便具有这种极富表现的力量。“敲”字以通感手法将钟声具象化,赋予击落明月的动态力量;“铺”字拟霜为绸,展现秋色延展的静谧感。二字动静相生,“敲”破夜空之寂,“铺”展天地之阔,使无形之声有色,静态之景含势。炼字之妙尽显时空交织出的一种禅境。全联语言简洁凝练,短短十四字,通过对寒山寺的钟声、月色、霜色以及秋景的描绘,将寒山寺的清幽、秋夜的寂寥都表现得淋漓尽致,构建了一幅动静交织的时空画卷,妙不可言。
再谈“精当”。这里是指选材精当,就是选择素材不仅要符合主题要求,还要符合四周环境的要求。这就是合实际、符事实,切实情的写照。譬如趵突泉观澜亭联:“三尺不消平地雪;四时常吼半天雷。”此联描绘了趵突泉从地底喷涌而出的壮观景象,泉眼处仿佛堆积了三尺多高的白雪,终日不融;四季流淌的水声宛如半空中轰鸣的惊雷,持续不断地回响。运用比喻和夸张的修辞手法,生动地表现了趵突泉的清澈水质和响亮水声,与其“天下第一泉”的美誉相得益彰,引人入胜。此联抓住了“喷浪如雪”“泉声如雷”的两个特点,足见选材精当。再看拙作《题石山书院》在选材上也是独具匠心:
岐阳之鼓,泗滨之磬,韵振五经之石;
鹿洞之风,岳麓之华,云藏万仞之山。
此联虽然句脚为“猪鼾式”,用典不宜移字,只好将就将就。但全联在“石”“山”二字上做足了文章。上联写石,“岐阳之鼓”,即石鼓文。“泗滨之磬”为泗滨石所作之磬。“五经之石”特指东汉熹平石经。“韵振”二字出《列子·汤问》“抚节悲歌,声振林木”,暗合《乐记》“声成文谓之音”的乐教传统。下联写山,“鹿洞”是指白鹿洞书院,在庐山,“岳麓”是指岳麓书院,在岳麓山。加之“云藏之山”取典司马迁藏史书于名山的典故。全联将“石”“山”二字嵌之其尾,即成雁足格。此联在运用典故和选材上都是生动准确、形象逼真且意义深刻的,显然是经过作者集中、取舍、提炼之后才运用到作品之中的,完全是为“石山书院”量身定度的,同时也反映石山书院深厚的文化底蕴,令人有“高山仰止”之感。
最后谈“精深”。精深主要是从作品立意上来说的,为文者,立意为先,意在笔先,而后措辞。立意就是写作意图,是思想,是格局,是眼界,是心胸,是灵魂。可见,立意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底色、情感倾向和价值取向。立意高远者,则文气象自具。譬如清代鄂尔泰《题菜圃门联》:“此味易知,但须绿野亲身种;对他有愧,只恐苍生面色多。”鄂尔泰作为军机大臣,他从菜圃之“菜”想到老百姓是不是“面有菜色”?这种恤民精神十分感人。此联在几亩菜畦间投射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精神格局,可谓是政治伦理寓言,足见情怀高,境界高、立意高。拙作《题橘子洲·江天暮雪》一联在立意上也是下足了功夫:
浮生如梦,人自倚,舟自横,零落天涯犹钓雪。
问我是谁,从何来,将何去?相看江上一蓑翁。
上联“浮生如梦”破题,以“舟自横”隐喻人生漂泊,“钓雪”意象将天涯沦落与寒江独钓并置,展现孤绝中坚守的傲骨。下联以诘问“我是谁”直叩存在本质,与“一蓑翁”意象形成观照,暗示答案不在追问而在自然真境。全联通过虚实相生的水墨意境,构建出世入世的精神对话,既含庄子齐物之思,又具禅宗当下顿悟之趣,最终指向天人合一的超然境界。全联以超逸笔调抒写人生哲思,立意深邃而高远。
对联犹如微雕艺术,每个字都要承载多重意蕴和意象,创作者须具备炼字成金的功力,同时,在平仄对仗的框架中,还要选择合适的材料加工和整理,让一句都成为多棱镜,折射出丰富的文化光芒。更要以高远之志立其意,以深厚之情抒其怀。作联立意,譬如登山,唯有至顶,方能一览众山之小。
二、气
“气”从哲学上来说,气是构成有形有质之物的本原,它贯通于有形有质之物内外,周行不息,处在无穷尽的变化之中。《周易参同契》中说“气”是:“抟之不得,视之不见,而能潜随化机,生成万物。”就是这种观点的体现。而将“气”的概念引入文学领域而研究的,是三国曹丕,他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:“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可力强而致。”意思是说,每个人文气不同,风格不同,外力是无法强行改变的。于对联创作而言,我认为“气”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:一是气韵,二是气势,三是气象。下面我们便分别展开来详细阐述。
首先说“气韵”。《南齐书·文学传论》云:“文章者,盖情性之风标,神明之律吕也,蕴思含毫,游心内运,放言落纸,气韵天成。”气韵于对联创作而言,就是要求上下联之间的内容、情感要连贯,一气呵成。无论是正对、反对还是流水对,都要做到逻辑自洽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有言:“情与气偕。”就是指情感流动与语言节奏的有机统一。宋代严羽更以“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”比喻其浑然天成的流畅特性。譬如我国近代民主革命家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李文甫的联句:“绿水本无忧,因风皱面;青山原不老,为雪白头。”此联以拟人化笔法贯通气韵,赋予山水灵动的生命节律。“绿水”因风生皱,“青山”为雪染白,一虚一实,逻辑自洽,将自然现象与人生况喻浑然一体,十分流畅。这里以拙作《联题大围山七星岭》举例来说气韵流畅的作用,试看:
独立斜阳,山如海,月似钩,一川星斗凭谁钓;
长歌旷野,云作裳,风为袂,万壑春花带醉呼。
此联以时空流转为脉络,上联由“斜阳”暮色切入,“山如海”拓开空间苍茫,“月似钩”引动星垂平野,至“凭谁钓”收束为天人对话的孤绝,气脉自黄昏向星夜延展,暗合南朝齐梁谢赫《六法论》“随类赋彩,气韵周流”之理。下联“长歌”破静,以“云裳”“风袂”化自然为衣冠,万物皆着我之色彩;末句“万壑春花带醉呼”,借酒意将山河点染为狂草笔势,虚实互用,疏密相间。有严羽《沧浪诗话》所言的“空中之音,相中之色”之通达。全联以钓“星”呼“春”之动势遥应,平仄起伏,形成呼吸般的韵律,又有唐代张彦远“形神兼备,生气灌注”之流淌。
再谈“气势”。这里是指上下联在气势上要连贯,不能上联力强,下联力弱,也不能上联境高,下联境低。也就是说上下联在情感、意境、力度上要气势相当,协调统一,不能锱铢不称。譬如网络联句:“气凌衡岳三千丈;心托桃花一两枝。”此联意境尚佳,不过气势不等,上联雄浑壮阔,下联纤巧婉约,这种从“气吞山河”到“心寄微物”的陡转,在审美张力上出现了断裂,从而形成了上下联气势失衡的问题。再看清代蒲松龄的自勉联:“有志者、事竟成,破釜沉舟,百二秦关终属楚;苦心人、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。”上联借项羽破釜沉舟的典故,展现出其勇往直前、决战到底的豪迈气势,最终成就霸业;下联用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,表现出勾践忍辱负重、刻苦自励的坚韧气势,最终实现复国大业。上下联都借助历史上的励志故事,以强大的情感力量和坚定的信念,营造出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强大气势,而且两者气势相当,相互映衬,激励着人们为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。试看拙作《题张家界天门山》一联:
天隐几多象,幻作雾和云,霞和日,时灭时明,世间一目孰参透;
门依十六峰,偕来风与月,泉与松,或空或远,胸次千寻任展看。
上联以“天”统摄,聚焦动态天象的变幻(雾、云、霞、日),构建纵向的宏大维度;下联以“门”为基点,依托静态山川的稳固(十六峰、泉、松),铺展横向的广袤空间。二者形成“天-地”垂直轴与“山-门”水平轴的立体交织,恰似中国山水画“高远”与“平远”的构图融合。另外上联以“孰参透”收尾,抛出对宇宙奥秘的终极追问,带有屈原《天问》式的哲思锐气;下联以“任展看”作结,展现与天地共游的豁达襟怀,颇具苏轼《赤壁赋》“物与我皆无尽”的超然境界。从气势上来看,上下联也是十分相当的。
最后说一说“气象”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以“盛唐气象”概括唐诗雄浑开阔的美学特质。文学意义上的“气象”是指作品整体的精神气质与艺术境界。好作品的“气象”除了自身独特的气质外,更是“万千”变化的,即意象的多重性与复合性。好的对联往往通过意象的叠加、引申、裂变,在有限的文字中构建出无限的精神空间,形成“咫尺万里”的审美张力。譬如,清代周元鼎《岳阳楼》联:“四面湖山归眼底;万家忧乐到心头。”此联的“气象”既非单纯自然景观之壮美,亦非狭隘个人情感之抒发,而是通过“湖山”与“忧乐”的辩证关系,将千年民生疾苦浓缩于方寸灵台,将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熔铸为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。这种气象万千的美学意象,重复叠加,给人一种“观物取象”丰富表现。在这里,同样以拙作《夜读有记》联来加以说明:
家乡霜月来温枕;
墙角蝉声伴读书。
此联以夜读为轴心,构建起跨越时空的多维意象,在方寸之间铺展出一幅流动的立体画卷。上联主要意象是“霜月”和“温枕”。霜月给人清冷、孤寂的感觉,却用来“温枕”?形成一种矛盾修辞,表达游子思乡的温情与现实的孤冷交织。下联也是如此,通过“蝉声”隐秘地表达了虞世南“居高声自远”和骆宾王“无人信高洁”的精神境界,同时表现王籍“蝉噪林逾静”的恬然心境。全联通过“霜月”“蝉声”物象对比,“温枕”“伴读”虚实结合的多重解码,彰显出“即景会心”与“格物致知”的思辨。如同文人书房里的一方端砚,既盛得下银河清辉,也研得开春秋大义。从而让意境翻新,形成了气象万千、意象丰富的独特风格。
文气的贯通如同书法中的“一笔书”,看似断开的对句实则暗藏气息流转。创作者需把握节奏的疾徐顿挫,让静态的文字产生动态的韵律,使对联成为可以呼吸的生命体。这种“气”的运行,既体现在句内逻辑的连贯,更在于句间意脉的暗合。
三、神
“神”可意会,不可言说,似有似无。《易·说卦》说:“神也者,妙万物而为言者也。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:“文之思也,其神远矣。故寂然凝虑,思接千载;悄焉动容,视通万里。”此话真是妙不可言。他强调艺术想象是无限的,静思可连接千年之久。想象可观万里之外。这种状态,也就他所说的“思理为妙,神与物游。”观点。即人的精神与象物的自由的交融之后,达到了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境地。于对联创作而言,我认为“神”也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读:一是神采,二是神韵,三是神化。下面我们便分别展开来详细阐述:
首先谈“神采”。在艺术领域,“神采”也是艺术核心指标。南朝书法家王僧虔在《笔意赞》中提出:“书之妙道,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。”在对联创作中,“神采”是其灵魂的外在表现,是其从内而外所传达的意境、气韵与精神境界。好的对联往往能以有限的文字,承载无限的精神意趣,甚至超越时空,直抵人心。譬如清代林则徐的联句: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;壁立千仞无欲则刚。”此联上联化用《尚书·君陈》:“有容,德乃大。”以“海纳百川”的包容气象,强调胸襟开阔;下联化用《论语》:“枨也欲,焉得刚?”借“壁立千仞”的险峻山势,彰显刚正不阿。此联的神采,正如其笔下山海,将儒家精神与天地气象融为一体,赋予了撼动人心的视觉冲击力,最终在人的心灵深处树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。再列举拙作《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》加以说明:
肝胆付丹青,将七十二衡峰,八百里洞庭,华封三祝;
河山如带砺,有五千年毅魄,九万重浩气,砥柱两间。
此联以山河为骨:取南岳群峰之巍峨、洞庭湖泽之浩瀚为地理坐标,以“七十二”“八百里”等虚数强化空间延展性,使具体山水升华为中华疆域的象征。以魂魄为脉:借《庄子》“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”之语势,将浩然正气量化为层叠奔涌的浪潮,暗喻民族复兴的磅礴动能。以祝颂为魂:借《庄子·天地》尧帝受“多福、多寿、多男子”之祝,此处转喻对国运昌隆、人民康乐、文明赓续的现代性祈愿。另外,“河山如带砺”化用《史记》:“使河如带,泰山若砺”的典故,将山川永恒性与国家长治久安相勾连,暗含对政权稳固的祝祷。此联神采如青铜鼎铭,超越性地将传统祝颂转化为现代国家叙事——山河不仅是自然存在,更是民族的精神图腾;历史不仅是过往云烟,更是奔涌向前的“浩气”。字里行间如见巨幅青绿山水长卷徐徐展开,在“丹青”笔墨与“带砺”金石之声的交响中,作者完成了对新中国75载征程的崇高礼赞。
再谈“神韵”。如果说“神采”是一幅作品外在的美丽“仪容”,那么“神韵”就是作品内在的独特“风格”。清代王士禛在《带经堂诗话》提出“神韵说”,主张诗歌应如“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”,追求“不著一字,尽得风流”的含蓄美,这种思想投射到对联创作中,体现为通过意象组合构建多层意蕴空间,从而实现其文本精神内核的铸造和风格的体现。譬如清代阮元题《杭州贡院联》:“下笔千言,正桂子香时、槐花黄后;出门一笑,看西湖月满、东浙潮来。”此联有神韵,在于全联以举子考试为支点,撬动起天时、地理、人文的宏大叙事。桂香槐黄见证笔墨耕耘,月潮交响消融得失执念,最终在“出门一笑”的瞬间,实现从“科举牢笼”到“天地大观”的精神飞跃。细细品味,的确有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艺术张力。试看拙作《代友挽柳斌教育部总督学》:
杏坛失师表,我自失形神,相忆如昨年,泪洒长天犹不尽;
折柳悲灞桥,招魂悲栗水,奈何在今夕,梦回万里已无他。
全联选用“杏坛”“折柳”“招魂”等典故,构建起文教传承的意象体系,试看,“杏坛”呼应孔子讲学传统,彰显逝者教育家的身份;“折柳”既扣姓氏又喻离别,暗合《诗经·采薇》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”的意境;“招魂”典出《楚辞》,强化悲怆氛围。而“栗水”为逝者故乡,使哀思更具体可感。结尾“梦回万里已无他”与上联“泪洒长天犹不尽”形成空间与情感的双重呼应,情感真挚。此联的神韵,在于将挽联常见的哀悼程式转化为文化基因的激活实验。在“泪不尽”与“梦无他”的终极悖论中,既完成对逝者的诗意安葬,更实现了对教育家精神不朽的庄严确认。
由此可见,这种神韵的营造,需要创作者跳脱文字表象,在文化基因与生命体验的交汇处开凿灵感的泉眼。让对联的意境突破时空界限,与读者产生精神共鸣。
最后谈“神化”。文学的“神化”,即出神入化。这里至少包含两层意义,其一是技乎其神,技巧变法近乎神工。如苏东坡在《答谢民师书》所言“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其二,情志潜移默化。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有教化功能的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说,“文须有益于天下,有益于将来。”就是强调文章的教化,并明确指出文章应该是。“明道也,纪政事也,察民隐也。”我觉得一幅作品最成功之处,就是“文以载道”,如果情志不在于中,技乎其神也是枉然的。试看《武侯祠联》:“收二川,排八阵,六出七擒,五丈原前,点四十九盏明灯,一心只为酬三顾;取西蜀,定南蛮,东和北拒,中军帐里,变金木土爻神卦,水面偏能用火攻。”此联以数字“一至十”嵌入上联,聚焦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、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。下联嵌入“东西南北中”及“金木水火土”,强调诸葛亮的外交策略与军事智慧,技法上可以说近乎神工,但情志何在?能隐喻什么?折射什么现实?显然没有!尤其是“点四十九盏明灯”与“一心只为酬三顾”二句没有因果关系,有强凑之嫌,另外“变金木土爻神卦”一句有隔,全不在眼前,又有堆砌之嫌。而明代顾宪成《东林书院》联: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。”上联以“风声、雨声”象征自然与社会的纷繁万象,而“读书声”则代表士人对知识的专注追求。三“声”叠加,强调学者需在纷扰中保持定力,以“格物致知”的态度治学修身。下联由“家事”推及“天下事”,主张学问必须与家国命运结合,并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精神力量,教化民众,开启民智。再举拙作《联题越南下龙湾天堂岛山顶之亭》说明:
眼底沧溟如一勺;
胸中丘壑接重洋。
此联上联以自然景观为媒介,展现了山水之壮阔。“沧溟”(浩瀚海洋)与“一勺”(微小容器)形成强烈对比。站在山顶俯瞰,浩渺海洋竟似一勺之水,既夸张地凸显观者立足之高的超然视角,又暗含道家“以道观物,万物皆小”的哲学观。下联转向内心世界,“丘壑”原指山水画中的构图布局,此处喻指人的思想格局;“接重洋”则打破地理界限,将个体胸怀与浩瀚海洋相连。正如陆机《文赋》中所说的“观古今于须臾,抚四海于一瞬”文人理想,暗含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责任意识,强调精神境界的无限延展性,与顾炎武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此联通过“自然之境”与“心胸之境”的互动,暗示士人“心包宇宙”的理想人格。最终达成“咫尺联语,万里江山;片言居要,百代心传”的文化使命。
综上所述,对联的精气神,犹如道家修炼的“炼精化气,炼气化神”过程。精是根基,气是桥梁,神是彼岸。虽然全文是掰开了揉碎了来阐述的,但三者是一个有机整体,相辅相成,互相作用的,不可分割开来。当代对联创作者在继承传统法度的同时,更需以现代思维激活古老形式,让对联艺术在保持“精气神”本真的前提下,绽放出契合新时代脉搏的作品之花。
(此文已在《对联》《楹联博览》刊发,此文为完整版)
上一篇 : 中交三公局三公司黄石公路项目发展大道高架桥完成主体结构施工
下一篇:草本香里学养生,中医智慧魅力强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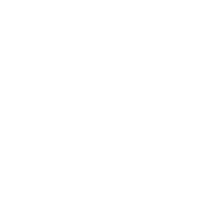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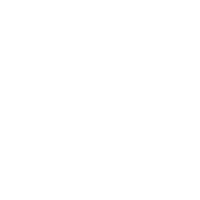
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42708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42708号